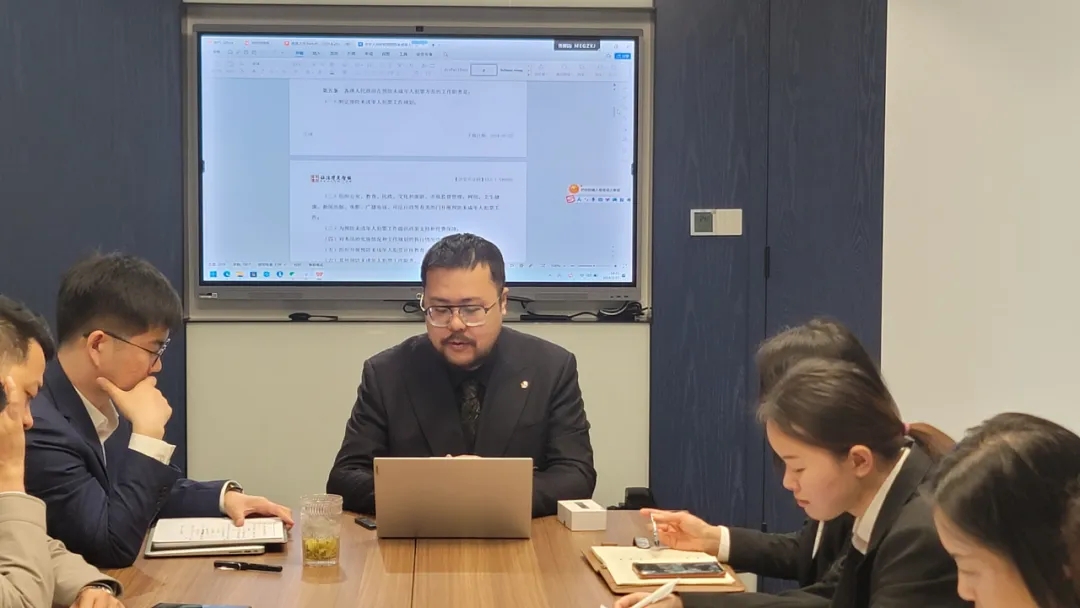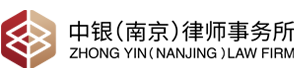郝煜洋:我不认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改,我认为这是立法对民意的一次过度退让。刘康乐:人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长大的,14周岁生日零点前后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刑事责任的承担一定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边界线,保证刑事责任适用的准确。张雨潇:作为普通民众的一员,我当然希望正义能得到伸张;哪怕是未成年人,有些时候有些人也可能会非常的邪恶。王杰:对于那些没有深入、系统学习过法律的普罗大众来说,杀人偿命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法律因为种种原因失灵了,我是支持法外复仇的。王晓影:现实情况就是,有些人是没有挽救的空间的。如果这一次放过他了,下一次他会更猖狂。刘康乐:立法者所考虑的是更高位阶的价值,譬如社会整体的秩序。而个人的情感与这些价值相比较,可能就会被立法者所放弃。宗原:面对霸凌事件,如果有人跟你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就应该一个巴掌扇他脸上,然后问问他,响不响?刘康乐: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去模仿、照搬我们自己的父母当年对我们的教育模式,机械地把子女培养成下一个自己。董昊:作为律师,作为父亲和母亲,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好,我们要这本律师证又有什么用呢?


宗原,中银南京所青工委主任,文化与体育法律业务部主任。吴淑豪,中银南京所青工委副主任,监事,企业刑事合规与反舞弊法律业务部主任;董昊,中银南京所青工委副主任,涉军法律业务部副主任;
宗原: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中银青年圆桌。今天的主题是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宗原:由于不久前在邯郸的发生某起恶性案件,未成年人犯罪再次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出于职业的谨慎和操守考虑,在没有看到任何案卷材料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对某个具体的案件进行任何凭空猜测和点评。今天的圆桌内容,是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这个社会问题、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是与非
宗原:首先,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律上最根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刑事责任年龄这个法律制度。相信即使不是法律从业者,经历了近年来多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所引发的重大社会舆论,社会民众对于这个制度多少也有所耳闻。
郝煜洋:在2020年之前,我国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长期以来是分为三个区间:已满16周岁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未满14周岁的,不负刑事责任;而位于两者之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仅对八种严重罪行负刑事责任,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郝煜洋:而到了2020年,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出台,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又增加了一个区间,即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郝煜洋:刑法修正案(十一)之所以会改变此前长期以来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其导火索是发生在大连的一起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案件。2019年10月20日,大连一名13岁的未成年人蔡某某,残忍杀害了一名10岁的女童。案发后,蔡某某不仅毫无悔意,甚至态度十分嚣张。而他嚣张气焰的根源,正在于他明知自己未满14周岁,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郝煜洋:大连这一案件当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也成为了刑法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导火索。案发一年后,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增加了12至14岁这个新的年龄区间。这次邯郸的这个案件,最高检就需要通过这个新增的条文来核准追诉。郝煜洋:但是,我个人并不认同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修改,我认为这是立法对民意的一次过度退让,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不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郝煜洋:我认为如果某个案件的行为人没到刑事责任年龄,因此不用负刑事责任,这不是一个法律漏洞。就比如原本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4岁,那行为人如果没到14岁,他就是无罪的。这就是刑法跟民法不一样的地方,刑法是一个刚性的法,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民法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比如中国大陆的民法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大陆法系,而拿破仑民法典第4条就明确规定,法官不能以没有法律或者法律不明确、不完备为由而拒绝受理案件。郝煜洋:但刑法不一样,刑法的核心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如果刑法规定未满14岁不承担法律责任,那未满14岁的行为人就是无罪。如果认为像大连那个案件一样,未满14岁的行为人做了那么恶劣的行为却不负刑事责任,如果认为这是一种法律漏洞,那么刑事责任年龄就会变成一个无底洞。因为只要这个制度不能包含某一个具体的恶性案件,人们就会把它视为一种不完善的立法,对这个制度永远都会处于一种质疑之中。郝煜洋:但如果从罪刑法定的刚性的角度来看,行为人没到那个年龄,那他就是无罪的。当然这个视角可能比较理性或者说比较冷血,跟我们国家的主流观点可能不一样。我们的主流观点是出了事必须要有人负责,所以我国大陆的刑事案件无罪率非常低,我们的文化不太允许有无罪的空间,所以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吧。宗原:郝律师这个意思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今天有一个13周岁的行为人做了这么一起恶性案件,我们就把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12周岁;如果明天有一个11周岁的行为人做了这个事情,我们再把它下调到10岁;后天再有个9岁的行为人呢?这就面临一个不断下调的问题,就会影响刑法乃至整个刑事法律制度的稳定性、确定性。宗原:但是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年龄的下限其实不是一个“无底洞”,这是有尽头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直接一次到位,把这个下限拉到底,换句话说其实也就是直接取消刑事责任年龄?王晓影:这就涉及到法律冲突问题了,我们既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又有刑法,这就是保护和惩罚到底要侧重于谁的问题。王晓影:因为我们有单独的立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但是又有相应的法律对未成年人的违法和犯罪进行处理,它本来就是一个侧重于保护,一个侧重于惩罚,它两个的立法目的就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现在如果直接全部取消,就只有惩罚没有保护了, 董昊: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会把未成年人变成一个犯罪工具。王晓影:对,这个有可能,会出现成年人利用未成年人,教授他一个犯罪方法,然后未成年人就成为单纯的犯罪工具,就相当于忽视了这些未成年人的基本人权。

刘康乐:我觉得要考虑到刑法、刑事责任它本身的功能是什么,除了惩罚、威慑、震慑之外,其实也有教育的功能在里面。未成年人毕竟涉世未深,可能对自身行为的后果及意义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认识,所以在社会看来他是有改造空间的;而且他未来的路很长,直接对他适用刑事责任的话,可能会导致他未来都融入不了社会,今后的人生就跟社会脱节了。这样的话,刑法的这个改造、教育的功能就是失败的。
宗原:那有没有可能这样来操作:我们不做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而是在具体案件中让法官根据证据情况去判断,这个行为人在主观上到底构不构成所谓的犯罪故意。如果确实因为年龄较小、心智发育完全不成熟,行为人完全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那就是不具备犯罪的构成要件。而像大连案、邯郸案这种明显清楚自己行为性质的,就正常去追诉。郝煜洋:有一种观点,就是建议引进欧英美法系那种恶意补足制度。恶意补足制度就是说行为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原则上是不负刑事责任的,但是如果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他有足够的恶意的话,就可以让他负刑事责任。但是这个制度和英美法系的其他制度一样,它都有很大的评估性。在我们国家这种司法的环境之下,或者说司法执行力上,靠这种评估来确定一个案件的走向太过于弹性了,这种弹性又可能导致权力寻租的这个空间,可能滋生司法的腐败。王晓影:对,这种方式最后可能会导致权力寻租的问题,如果把这个权力全部下放给法官的情况下,那法官的裁量权就太大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也就会变大。行为人的家属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影响法官,让他做出一个对孩子有利的判断。刘康乐:刑事责任年龄在我国古代的立法、司法中也有相应的体现;比方说在西周有一个三赦的制度,其中第一赦就是幼弱,就是对于年幼、体弱的人,是给予赦免的。这个制度在此后历代也是一直有所延续,比如汉朝,未满七到八岁的未成年人,除了故意杀人之类的重罪之外,也是可以不予追究的。所以我觉得刑事责任年龄这个制度,并不是近代凭空产生的一个新构想,它其实在我们古代的立法制度里面都有相应的体现,本身是一种立法文明的体现,能够彰显刑法它的教育和矫治的功能。刘康乐:但是到底定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才算合适,这个我觉得从立法技术上来讲,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因为人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长大的,13周岁和14周岁的人有什么区别吗?因为过了0点那个生日,你的思想、意识就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吗?但是刑事责任的承担一定是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年龄放在这里,保证刑事责任适用的准确。 刘康乐:所以出于这个考虑,法律只能通过一个一刀切的设计,确定一个立法者认为行为人应当认识到自身行为的意义与后果的年龄。至于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这个区间,我觉得它一方面是考虑到这种一刀切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也是体现立法者要让刑法适用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相适应。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这个改动还是比较成功的。
宗原:刘律师刚刚提到社会的发展,我最近因为邯郸案件,再次看到一个观点:在以前信息流通并不发达的时候,可能除了从业者之外,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刑法的相关规定都不是很了解;但是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和普及,小朋友们都是人手一个手机,天天泡在网上;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通俗来讲就是我14岁以前或者12岁以前杀人不犯法,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明文规定,可能反而会去刺激或者是纵容一些潜在的未成年人,让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实施犯罪。
张雨潇: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不光是我国,欧美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青少年是你最不能得罪的人,因为法律对他们有特殊的保护,你们在法律上不是一个对等的地位。而青少年自己也是知道这些信息的,他会知道在这个年龄段我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责的。再加上青少年心理发育可能相对还不成熟,本来就容易做出一些冲动的行为。张雨潇:大陆法系的国家,比如说像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采用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14岁的这个标准,也就是我国在2020年之前的标准。而像委内瑞拉、葡萄牙、墨西哥、牙买加等国的最低标准是12岁。我们东亚邻国日本自从2007年修订少年法之后,把最低年龄从刑法典规定的14岁,实质上修改到了11岁。张雨潇:美国的情况则相对比较特殊,因为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立法权。美国各州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普遍在10到12岁,而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州反而更低,比如纽约州的规定是7岁;这也是考虑到经济发达地区的未成年人接触信息的渠道比较丰富,容易受到蛊惑和腐蚀。

宗原:那么张律师你个人对刑事责任年龄的看法是什么呢?你觉得应该设立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吗?
张雨潇:我认为不应该设立,尽管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说得通俗一点,犯罪就该治。很多时候感化和教育是行不通的,反而是严厉的惩罚更能阻止潜在的犯罪行为。作为普通民众的一员,我当然希望正义能得到伸张,我也知道哪怕是未成年人,有的时候也可能会非常的邪恶。张雨潇:那当然。总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至少在立法层面,欧美发达国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应对方法,只能是建议成年人尽量容忍、回避。而这或许也是我们将来要面临的情况。叶家丽:提到欧美国家,还有一种做法是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说7岁以下是不承担刑事责任,7岁到10岁可能就是不采取强制措施,10岁到14岁采取恶意补足的法律概念,让法官来进行评估,最后14岁以上是正常承担刑事责任。此外,在刑罚的操作上也是比较灵活的;譬如原本判处有期徒刑的,可以通过缴纳罚金或者参与社区服务的形式来替代,免于牢狱之灾。而这种替代刑,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下可以更加广泛、高频地适用。

宗原:近年来每次出现这类恶性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舆论上都有一个常见的观点,就是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实际上保护的是未成年罪犯,而不是未成年受害人。当未成年罪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遭到应有的制裁,甚至是逍遥法外的时候,法外复仇的火种可能便就此点燃了。而对于这种法外复仇的行为,社会舆论和司法实践上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和分歧的。
王杰:作为法律工作者,可能天然会有一种思维,觉得法外复仇是不对的。但如果是跟那些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律的普罗大众交流,他们可能会觉得杀人偿命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近年来就有两个影响力较大的案例,分别是张扣扣案和于欢案。王杰:张扣扣是陕西汉中人。1996年,张扣扣之母与邻居产生纠纷,被邻居家三儿子用木棒砸死,当时张扣扣年仅13岁。因邻居家三儿子当时未成年,法院对其从轻处罚,仅判处有期徒刑7年。但张扣扣一家始终坚称,当时的行为人实际上是邻居家的二儿子,三儿子实际上是利用其未成年身份为兄顶包。王杰:此后,张扣扣始终怀恨在心。22年之后,2018年2月15日,张扣扣持刀将邻居家三人杀死,并将邻居家的小轿车点燃。2月17日,张扣扣自首。2019年1月,汉中中院以故意杀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张扣扣死刑。4月,陕西高院二审维持原判;7月,最高院核准死刑;7月17日,张扣扣被执行死刑。王杰:于欢案则发生在2016年的山东聊城。于欢之母因为此前借了高利贷,长期受到讨债人员的骚扰。2016年4月14日,在与母亲一起经历了11名催债人长时间的侮辱后,于欢掏出水果刀乱刺,致使4人受伤,其中一人之后因失血过多死亡。王杰:2017年2月,于欢一审被聊城中院判处无期徒刑。5月,山东高院二审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五年。2020年11月,于欢减刑提前出狱。
宗原: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假设有这么一个家长,他的孩子是某起极端恶劣的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而犯罪行为人是一个不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个未成年人清楚地知晓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主观恶性极大,但因为不满12岁,所以绝对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这种情况下,这个家长选择了采取极端的方式,向这个犯罪行为人法外复仇。那么,在座的各位会如何评价这位法外复仇的家长呢?
王杰:其实从张扣扣和于欢这两个案子的大众舆论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社会大众对于这种极端情况下的法外复仇是比较认可的。(宗:那你呢?)我也是一样的。如果法律因为种种原因,已经没有办法去实现它应有的目的了,而且这个案件情节也很恶劣,那我是支持的。郝煜洋:我感情上比较复杂。我认可他的做法,但是他做出这种法外复仇的行为,他自己最后肯定也要付出代价的,我又不希望他为了这个行为受到处罚。董昊:这个我肯定认同。

刘康乐:我觉得这是立场问题。只要是人,肯定是有那种原始的同态复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冲动,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讲是可以去理解的。但是作为律师来讲,为什么要有现在的司法体系,要有现在的那个刑法和审判制度,就是为了防止无休止的私力救济。你把对方杀了,对方家里再来人把你杀了,像这样无休止地厮杀下去,社会还有秩序可言吗?立法者的角度跟我们一般人肯定是不一样的,他所考虑的是更高位阶的价值,比方说秩序、公平;而私人的感情如果跟秩序这些价值相比较的话,可能就会被立法者放弃。
王晓影:我如果不是律师,情感上我肯定是支持的。因为这个犯罪行为人他不吃点苦头,如果这一次放过他了,他下一次会更猖狂。至少从我办过的案件来看,只要犯过一次这种错误的人,他的胆子是会越来越大的。我们讲惩罚也好,教育也好,现实情况就是,有些人他是没有挽救的空间的。一个人各个方面的形成,最终都是多因一果的,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作用力或者哪一个因素,最终就会导致它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了。叶家丽:作为律师,我理解他想复仇的心情,但我不建议他去法外复仇。作为他的朋友,我不希望他背负那么多。不只是后续会产生的法律责任上的代价,还有心理上的负担。
王晓影:但是对于这个家长来说,我想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去下手之前肯定是已经想好了;你所谓的心理压力,其实在他下手之前肯定已经考虑过无数次了。成年人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他需要选择是明哲保身、无所作为、在这种痛苦中生活下去,还是说去法外复仇,宁肯遭受法律的制裁也要实现自己心中的正义。
张雨潇:作为旁观者,这个家长如果问我一些问题,我会给他提供法律咨询。有些事情他自己不做,可能这辈子都走不出来了;这条路走到黑的话,哪怕最后他要承担不好的后果,但这个心结他就已经放下了。王伊妮:我的态度就是尊重吧。我觉得他不需要我的认同,我会选择不干涉、不影响。
三、未成年犯罪的预防
王伊妮:从最近这几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双方的家庭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这些加害者的家长,对孩子往往是极端地纵容、溺爱甚至是包庇。另一方面,这些受害者,尤其是一些长期霸凌的受害者,他们的家长往往对他们缺少关心和重视,尤其是缺少对校园霸凌行为的警觉。甚至可能直到发生了恶性刑事案件,家长才知道存在霸凌情况。
王伊妮:从这个方面来说,家长还是需要和孩子多进行沟通,以身作则、让孩子成为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同时,更要让孩子敢于告诉家人,自己在校园里遭遇了什么,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张雨潇:就我个人观察到的情况而言,我身边有孩子的朋友,他们现在往往会送孩子去学习一些防身的技能。一是能提高小朋友的身体素质,二是给小朋友一个最起码的保障。当然我们不提倡用暴力解决问题,但如果真到了极端的情况,起码要具备一定的自保能力,而不是只能用言语和礼貌去面对别人的拳脚甚至凶器。
董昊:(我所知道的)现在几乎所有的家长,给孩子的教育都是,对方欺负你了,那你一定要反抗,不能任人欺负。
王晓影:确实,我们小时候大部分人接受的教育,都是要我们尽可能地去容忍;别人欺负你了,你就去找老师或者找家长,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处理。而现在的家长往往会让孩子首先进行反抗,之后再去谈判桌上解决问题。董昊:是的。我们小学班主任在班上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叫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宗原:这其实和实务中正当防卫难以得到认定、一旦还手就被定性成“互殴”是一个道理。实际上是管理者为了降低管理的成本和难度,用这种方式让老实人去吃亏、去让步,整体上减少冲突发生的概率。这绝对是一种非正义、非道德的管理方式。王伊妮:有些老师和家长甚至会说,你如果不惹人家,人家怎么会打你,所谓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宗原:面对这种霸凌事件,有人跟你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就应该一个巴掌扇他脸上,然后问问他,响不响?(笑)刘康乐:考虑到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个人觉得,想要从法律层面上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效果可能不会特别理想。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从文化、制度上去去想办法。比如说我国自古以来都有一个家族的观念,大家族里家长的示范作用和对晚辈的约束作用都是很重要的。四川地区的一家监狱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们监狱内的未成年罪犯,家庭存在严重问题的占比超过50%。作为家长,我们可能也需要定期去反思自己,定期去参加一些培训的课程,去学习怎样和子女沟通、该树立怎样的教育理念。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去模仿、照搬我们自己的父母当年对我们的教育模式,机械地把子女培养成下一个自己。刘康乐:至于学校方面,虽然现在学历贬值严重、学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学校还是不能忽视对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和指导。学校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情况,尽可能地设立和普及心理辅导老师和心理辅导的课程。刘康乐:西方国家有一个制度,我个人觉得应该很有用。就是去培养大家回馈社会的理念,去安排很多社会服务的工作,把相应的工时纳入升学、就业的考评之中。我之前去甘肃出差的时候,参观当地博物馆,遇到一名大概七八岁的儿童志愿者,给游客讲解甘肃博物馆的历史。这个孩子虽然年龄很小,但是思路非常清晰,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如果让未成年人从小就去参与这种服务社会的活动,让他们接受优秀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这显然有助于从根源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王晓影:从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办理刑事案件的经验来看,在实务操作中,公检法基本上都是倾向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般的未成年人案件,只要不是特别恶性的严重暴力案件,基本上一开始就会安排取保,让未成年人先去上学。甚至直到大学阶段也是如此,因为公安认为他们没有社会经验,对这方面的辨别能力不足。也就是大概在22岁之前,都处在这么一个保护期内,公检尽量不去进行羁押,法院最后往往也是判缓刑。
王晓影:我个人处理过的这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里,唯一一起我觉得确实没有挽救空间的,是一个未成年人贩毒案件。这个孩子的家庭条件其实是很好的,父母都是重要单位的公务员。但因为她父亲存在重男轻女的想法,为此和她母亲离婚,也由此导致了她严重的叛逆心理。她就觉得想要得到父亲的关爱,但通过正常方式是无法得到的;于是她频繁出入酒吧等场所,沾染了毒品,并最终从吸毒走上了贩毒的不归路。王晓影:公安机关其实也还是天然倾向于保护她的,但她的涉案情况确实过于严重。当时她是先在江苏这边服刑,刚出狱又被浙江公安带走,再之后又被湖北公安带走。再加上这个孩子也是始终在对抗公检调查,仗着自己是未成年人,态度颇为嚣张。

董昊:作为家长,尤其是做父亲的,一定要尽可能多参与孩子的生活,尤其是校园生活。我的父亲是一名长途大货车司机,每次出车往往都要一个礼拜之后才能回来,可他每次回来都会立刻去学校接我,这就给了我极大的安全感。
现在我有了孩子,我也是一样,尽可能多去接孩子,多去参与孩子学校的活动,让他的同学们和他自己都清楚地知道,他有我这个后盾。作为律师,作为父亲和母亲,如果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好,我们要这本律师证又有什么用呢?宗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的中银青年圆桌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活动组织:中银南京青工委、中银南京文化与体育法律业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