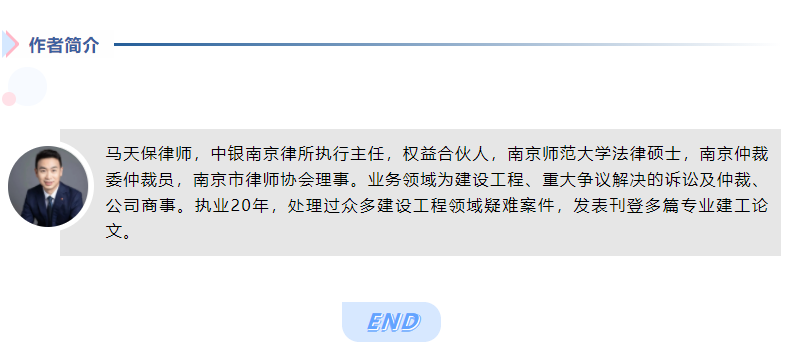案情介绍:
A公司(受让方)于2015年底与B公司(出让方)签订《增资并购协议》,约定A公司以1000万元收购B公司在目标公司全部股权,并就股权转让各个步骤达成一致。合同由两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后加盖公司印章。
后因目标公司过往经营问题,出现重大变故,致使《增资并购协议》未能按约定顺利履行。2017年5月,双方再次达成《补充协议》,约定因目标公司变更导致的履行障碍由B公司负责消除并承担损失。双方先行办理目标公司股权转让手续。其中,在80%股权变更资准备完成后30日内,A公司支付700万元转让款;在《补充协议》签订后12个月内B公司根据A公司要求配合办理20%股权变更手续,A公司于变更后5日内支付300万元股权转让款。B公司应采取措施消除目标公司遗留的问题。《补充协议》由双方法人签字加盖公司公章。
《补充协议》达成后B公司迟迟未能准备80%股权转让手续,也未能采取措施消除目标公司存在的遗留问题。2017年10月B公司上级集团上市公司出现重大财务危机,直接影响到B公司及其集团的合同的履约能力。为此,2018年1月8日,出让方、转让方签订《备忘录》约定,双方在目标公司开立共管账户,A公司暂时支付640万元转让款,待B公司消除目标公司遗留问题后,双方再多退少补。A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A公司签字,B公司所在集团总裁以及股权转让经办人、联系人共同代表B公司签字。后A公司将640万打入共管账户,并将账户电子密钥邮寄给B公司股权转让经办人,该经办人又将密钥交给集团总裁保管。
因B公司所在集团债务持续爆发,B公司经办人及集团总裁于2018年3月离职。因目标公司历史遗留问题,A公司支付至目标公司共管账户的640万元于2018年5月被查封冻结,后被法院全额执行;B公司于2018年6月起诉A公司,要求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
原一审、二审审理过程在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查明《备忘录》代表B公司的签署方是B公司股东即集团公司总裁及内控部总经理(以下简称“两名高管”),并非B公司的法人,也非B公司直接工作人员。B公司未给两名高管出具过授权委托书,《备忘录》上也未加盖B公司公章。一审法院认为两名高管不构成职务行为,且A公司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因此该两名高管也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A公司向B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并按银行双倍利息承担违约金。
A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以相同的理由,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再审审理情况A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申诉审查,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再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
经再审审理,高级人民法院最终采纳A公司再审意见,认定两名高管构成职务行为,2018年1月8日签订的《备忘录》对B公司具有法律约定力,据此撤销原一、二审判决,驳回了B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例评析本案争议点在于两名高管是否属于B公司工作人员,是否在执行B公司的工作事务?具体来说是2018年1月8日母公司两名高管代表B公司签订的《备忘录》对B公司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一、原一、二审法院判决理由分析
原一、二审判决认定《备忘录》对B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具体理由为:
1、B公司未向两名高管人员提供书面授权;
2、《备忘录》未盖章,不符合原两次签订协议均加盖公盖、法人章的交易习惯。
3、《备忘录》实质性改变了股权转让款的付款条件,损害了B公司的利益。据此,认定两名高管人员签订《备忘录》的行为,不构成履行职务行为。且因A公司未能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存在过错,因此,两名高管的行为也不构成表见代理。认定《备忘录》对B公司不具有法约束力,并按原《补充协议》判决支持B公司诉讼请求。
二、再审法院的判决理由
再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在认定原一、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的同时,补充查明以下三点原审判决遗漏的事实:
1、B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均为上级集团公司出资;
2、B公司认可两名高管为上级集团公司人员及担任的重要职务,且是本次股权转让的联系人、经办人;B公司内部为两名高管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北京缴纳了社会保险。
3、2018年1月8日《备忘录》签订后,B公司配合办理了全部股权转让手续,A公司向共管账户支付了640万元资金。B公司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行为,与《备忘录》约定一致,与原《补充协议》约定不一致,据此法院认定B公司以行为知道并认可《备忘录》存在。
再审判决,同时释明以下判决理由:
1、从《备忘录》签订主体看,两名高管所在集团是B公司唯一股东,两名高管与B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且为本次股权转让的联系人、经办人,《备忘录》同时记载两名高管是代表B公司签订。综合股权转让交易过程中,认定两名高管签订《备忘录》属于行使职权。
2、从《备忘录》内容看,事关股权转让履行进度、不畅原因、解决方案。股权转让不畅原因与案件查明的原因一致,是B公司违约且未采取补救措施造成。两名高管代表B公司商定的解决方案,是结合股权转让客观实际、目标公司存在的历史问题采取的务实方案,并无损害B公司的意思表示。
3、从《备忘录》履行看,B公司并未按原《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进度办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而是按照《备忘录》的约定,在未直接收到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配合办理了全部目标公司股权转让,A公司也是按照《备忘录》的约定向共管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可以认定B公司知晓并认可《备忘录》。据此认定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与处理结果错误,予以撤销。
三、原一、二审判决理由与再审判决理由的对比分析
1、原一、二审判决重点考察两名高管外在授权和《备忘录》的形式表现。简单的从工作关系、是否盖章、是否有授权委托等形式表面,分析两名高管的行为性质,而没有深入分析两名高管与B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2、再审判决则从交易履约习惯、两名高管所在集团与B公司之间的关系、股权转让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具体细节、交易过程中各重要文件形成的原因、案件处理结果的实质性公平等角度,全方位考察《备忘录》是否能够代表交易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四、本起案件带来的启示
1、商事交易,应当重视外观表现。
基于保护交易相对方合理信赖利益,促进商业交易的需要,在商事交易和争议解决中,非常重视商事行为的外观表现。例如商事交易参与人一般需要明确的身份证明,公示信息与非公示信息不一致时,会以公示信息为优先考量因素。具体到本案,A公司在与B公司签订《备忘录》时,A公司只重视审查代表B公司的实质性授权即要求集团总裁签字,而忽略了形式上加盖B公司印章的重要性。如果不考虑本案交易过程中的细节,仅从《备忘录》本身来看,行为人对B公司的代表在表面上是存在瑕疵的。当然,任何行为的发生,都有其当时发生的合理原因。本案代表B公司签订《备忘录》的人员本身为B公司所在集团高管,且其中一名为集团“总裁”,并且全面负责交易的全过程,加之B公司与集团之间的关系,让A公司人员内心中根深蒂固地认为两名高管尤其是集团“总裁”具有签订《备忘录》的职权,而忽略了集团与B公司在形式上仍然为“两家公司”的法律事实。当然这与A公司人员本身相对缺乏商事法律常识也不无关系。正是由于A公司的这一“疏忽”,才引发一场历时四年的诉讼,且已经开始被强制执行。如不是再审及时撤销原判决,A公司不但将损失原支付的640万元,还要再支付股权转让款本息约1400余万元。教训不可谓不大。
2、应当从内外两个层面,探究“行为”是否能够代表被代理主体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能仅注重外观,不考虑内在实质。
《九民纪要》第41项谈到“盖章行为的法律效力问题”时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主要审查签约人于盖章之时有无代表权或者代理权,从而根据代表或者代理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合同的效力。”如果是明显无代理或代表权之人加盖的公章,“公章”也不能产生代表民事主体的法律效力。该条表明,在审查行为是否具有效力时,不但要审查外在表现,更重要的需要审查内在实质上行为人是否具有代表权或代理权。
公司等企业法人作为法律拟制的人,其意思表示均是以其工作人员的代表行为或代理行为作为表达形式。因此,有效的代表或代理与法人真实意思表示之间互为表里。只有有效的代表行为或代理行为才能表达法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理,能表达法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应当是有效的代表或代理行为。一般情况下,外在的代表或代理行为形式上具备合法要求,即可直接确定法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非存在相反证据。当外在“授权”形式存在缺陷或真伪难辨时,也要从行为当时的客观原因、各方主体具体履行进行综合考察。本案中仅从两名高管工作单位、书面授权来看,对认定构成职务行为存在重大障碍。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备忘录》签署后,B公司的具体履行过程就能发现,B公司在当时完全是按照《备忘录》在履行,这就能证明《备忘录》表达的是B公司认可的“真实意思表示”,两名高管的签署行为应当为有效的职务代理行为。原一、二审法院就是完全忽略了《备忘录》签署时的客观原因和具体的履行过程,而仅从行为人外在授权表现判定行为的法律效力,从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和法律适用错误。
3、应当从行为是否符合基本的商业逻辑,进一步判断行为的性质。
商事行为有其基本的内在逻辑规律,“营利”或者“有利”是商事行为的最基本特征。行为人在执行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职务行为时,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争取利益,是行为的基本价值取向。争取利益包括正反两个方面,正面包括直接、间接取得相应的利益,反面包括减少、停止相应利益的损失。而且判断是否行为有利或者能够获利,应当以行为当时的时空信息为判断依据,而不能以发生争议时是否有利作为依据。本案中,股权转让不畅的根本原因在于目标公司历史问题,而消除该历史问题是B公司本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因此,2018年1月8日签订《备忘录》,表面上看起来减少了部分价款,改变了价款支付方式,但实际上却是为B公司对前期的违约行为争取补救时间。两名高管代表B公司商谈、签订《备忘录》行为,仍然是出于维护B公司利益而实施的行为。再审法院的裁判理由之一即是《备忘录》记载的内容与案件查明的事实相符,两名高管协商“采取的务实方案,并无损害B公司利益的意思表示。”相反,如果《备忘录》中记载的内容并无事实依据,《备忘录》达成的新意思表示也损害B公司利益,而没有合理依据,这样的行为就是缺乏内在逻辑支持,如果再结合缺乏必要的外在授权,则就很难被认定为职务行为。因此,行为当时是否有利于被代理人,也是判断是否构成职务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
综上,本案作为职务代理行为的一个非典型性案例,出现了母公司员工跨公司实施职务行为,代表子公司签订合同这一复杂案情,在实务当中给予律师一个重要启示:在类似案件中要结合案件的全过程进行考虑,于细微处挖掘关键事实,而不局限于表面的案情限制,多维度考量行为的背后因素,才能为取得胜诉奠定基础。
参考案例:(2021)京民再158号。A公司代理人马天保、马洋,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